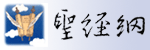翻譯與注釋
人類學家發現,在有些原始部族中,他們不同語言的族名,譯出來卻是同樣的意義,就是 “人”的意思。原來這些小部族有個共同的想法,以為唯有自己部族是
“人”!當然,在他們的思想中,他們的語言,也就是惟一的語言了;至少在跟別的種族往來之前,他們的思想是這樣的。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,越不堅持這種看法。
許多種族都愛他們自己的語文,認為他們的語文最優越。但這樣聲稱的人越多起來,達到共同結論的希望也就越渺茫。我們使用中文的人,也喜歡喜稱揚中文好,中華文化悠久光大;因為中文是世界上最多人用的文字。語文的功能既是表達思想,以使思想交流,當然使用的人越多,其可能發生的作用也越大,這就是好了。以宣揚福音的可能效用來說,中文也是效用最大。
但無論如何,生在巴別文化以後的人(參創一一:1-9),要使思想交流更遠更廣,必須承認在自己的語文之外,還有別的語文,那就需要翻譯了。作文字宣道工作,很顯然的,翻譯佔很重要的地位。
聖經中的但以理,可以作為翻譯人員的榜樣。
翻譯的準備
在猶大王約雅敬年間,但以理被尼布甲尼撒王擄到巴比倫。這是上帝的旨意,預備成就祂的旨意,其重要任務之一,就是作翻譯的聖工。
一.適當文化環境:但以理是以色列人宗室貴胄中,被擄到巴比倫去的少年人。在那異邦的環境中,他可以融合在他們中間,徹底了解他們的文化思想。在聖經中特出的領袖們,神所揀選的器皿,為世人預備救恩的,神都本乎祂的預知預定,安排最合宜的訓練環境。這是最確定的方法,知道神的呼召。約瑟被賣到埃及;摩西被法老女兒收養,長大在王宮;尼希米到波斯;但以理被擄去巴比倫;都是神所安排最合宜的環境,使他們從幼年熟習不同的文化。今天華人難民流寓全世界,正是學習適應各國文化的好機會,可能是神使華人從文化的衝激,認識福音的使命。
二.精擅不同語文:“王吩咐…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胄中,帶進幾個人來,就是年少沒有殘疾,相貌俊美,通達各樣學問,知識聰明俱備,足能侍立在王宮裏的,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。…滿了三年。”(但一:3-5)作翻譯工作的人,至少要兼通所譯的和譯成的文字。馬丁路德斥罵謔弄批評他德文聖經譯本的人,認為他們對語文瞭解不夠。約瑟的埃及語文程度,不但足使埃及人瞭解,甚至他的弟兄們聽不出來(參創四二:23)。摩西的語文程度,可以使他被認作標準的埃及人(參出三:19),可以在法老和希伯來人中間往返,傳達神的信息。保羅可以在雅典向希臘人講道,並且引用希臘文學作品,得心應手,用希臘文寫作。今天我們向華人傳福音,如果還需要人傳譯,那又成何體統!同時,我們要注意學習外文的認真態度。但以理以有智慧著稱(參結二八:3),“知識聰明俱備”,而且更在少年,尚且要用三年的時間,在王宮勤勉學習;如果以為只要每週上二小時課,混上一年,或去外國住了半載,便以語文專家自居,真是太過輕易了,近乎騙小孩子。不論你說怎箇屬靈,怎樣有神差遣的真憑實據,還是要在語文上好好下功夫。
三.通達各樣學問:語文是傳播的媒介工具,可以使人知道怎麼說怎麼寫,但還要有內容,說甚麼,寫甚麼。神的僕人不該以學問驕人,今代的學問浩瀚,也沒有人可以俱通俱備;但應有基本的知識,可以不輕易被人欺騙,不至鬧出笑話。千萬不要以無知識,反知識為屬靈;雖然知識學問跟屬靈不是一回事。
四.有神賜的智慧:人的努力和人的學問之外,更要有神賜的智慧,才足以擔負神的使命。“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,賜給他們聰明知識。”(但一:17)因為神是眾光之父,智慧之源。(參雅一:5,17)在翻譯中,有時翻查字典,搜索詞句,始終難找到適切的譯文;轉向神虔誠祈禱,就可得到音義俱佳的迻譯。
五.另有一個心志:“但以理卻立志,不以王的膳,和王所飲的酒,玷污自己。”(但一:8)但以理的處世,在於善用“不”字。約書亞和迦勒,告訴以色列民“不要背叛耶和華,也不要怕那地〔迦南〕的居民。”(參民一四:9)路得對婆婆拿俄米說:“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,…”(參得一:16)這都是另有一個心志,與眾不同的人,得著特別的福分。但以理立志持守聖潔,不染世俗罪污,才能得著聖善智慧之靈的做示。因為“敬畏耶和華,是智慧的開端。”(箴九:10)而“敬畏耶和華,在乎恨惡邪惡。”(箴八:13)如果有生命生活不聖潔的人,自稱得了“啟示”,什九是大有問題的。如果這種人從事翻譯工作,縱然他妙手能文,但有繡口而無錦心,到與個人利害攸關的時候,可能曲解謬譯,可以婉轉迴避,違背原意,自然難稱信譯。更糟糕的是,明明是曲譯,訛譯,卻要說是原作者的話,等於偽造假託,實在是不誠實的事。寫文章的內容好壞,功過都歸自己;翻譯卻有可能弄奸取巧,使人受過,自己居功。因此,我主張唯有誠實正直的人,可以作好的翻譯工作。這看來似乎是“文如其人”一元論老生常談,但在屬靈的事工上,是非常真實的。
翻譯的實際
但以理在老年的時候,作過一次很出色的翻譯工作。巴比倫末代的王伯沙撒,設擺盛筵,與臣僕群飲;在酒酣興高的時候,“吩咐人將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拿來,王與大臣皇后妃繽,好用這器皿飲酒”,並且歸榮耀給他們的偶像。“當時忽然有人的指頭顯出,在王宮與燈台相對的粉牆上寫字。王看見寫字的指頭,就變了臉色,心意驚惶,腰骨好像脫節,雙膝彼此相碰。”(但五:1-6)這真是驚人之筆,也真是大煞風景。,王和皇臣驚惶無措,還是太后舉薦但以理,因“他裏頭有美好的靈性,又有知識聰明,”“他裏頭有聖神的靈,…心中光明,又有聰明智慧,好像神的智慧。…”(參但五:10-12)於是,但以理被召到王和眾臣面前。神自己是作者,但以理作譯者。這樣的重要翻譯工作,非但以理這樣的人不能擔任。因為惟有“屬靈的人”有“從上帝來的靈,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。”(參林前二:10-16)但以理的翻譯:
所寫的文字是:“彌尼,彌尼,提客勒,烏法珥新。”講解是這樣:“彌尼”,就是上帝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;“提客勒”,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襄裏顯出你的虧欠;“昆勒斯”,就 是你的國分裂,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。(但五:25-27)
在這裏,引起我們思想翻譯上有關“直譯”與“意譯”的問題。如果直譯成“衡量,天平,分開”,而不用意譯,粉牆上的寫字,恐怕是徒勞無功,難以收到豫言見證的效果。有但以理的翻譯,才使意義顯明,“被稱在天平裏顯出虧欠”,也成為一般通行的語句。
馬丁路德的譯筆高妙。他在“論翻譯”文中,根據他自己把聖經譯成德文的經驗,說他經常以“純粹和清晰”為原則;有時會為了探求一個適切的字,而花上數週的時間,卻一無所得。但在另一方面,他謹守忠於原文,並不輕易忽視字面的意義,甚至有時不得不寧願破壞德文,而不願與字面分離。他認為“翻譯不是人人都能從事的一種文藝;它需要一顆真正虔誠的,信實的,勤勉的,敬畏上帝的心。因此我認為一個虛偽的基督徒,或激烈份子,不能作為一個信實的翻譯者。”(見湯毅仁譯:“論翻譯”載路德選集下,輔僑。98-99頁。)
華人講到翻譯,至今還有人常提起嚴幾道的“信,達,雅”三原則。這當然是內行人的最高理想,但只有外行人才去刻意吹求,因為實行起來很難。有過翻譯經驗的人都曉得,翻譯不是由一個字或詞,對譯成另一個字或詞,而是要引入另一種文化或思想。每有一字多義的,在譯文中不得不勉強取一種意義,而減其豐富。至於“雅”的標準,固然可因人而異,連甚麼是“達”也很難界定。而如果本來不“雅”的,勉強譯成“雅”,則不能“信”了。紅樓夢中的薛蟠,水滸傳中的李逵,從骨于子裏就不是“雅”人;如果譯者使薛二爺之言如孔子,李逵會“話不投機,拂袖而去”,那簡直是“殺”人物的暴行,而另作鑄型。馬克吐溫就是馬克吐溫,絕不應該譯成密爾頓的長詩莊嚴雄渾的拉丁文風格。桐城派夫子文體再高妙,也難把辣伯萊(Francois
Rabelais,C.1494-1533)的諷刺文章譯得傳神。就是嚴老先生自己的譯作,也“不能達到他所懸的標準。別的不說,“天演論”一詞誰還中意?豈不是因為不適者不存,天然淘汰了,由“進化論”取而代之?“群學肆言”與“社會學概論”比較,哪一個更“達”?
至於譯詩,更是難上加難。有人說,詩要譯得好,譯者要比作者是更偉大的詩人。這話看似誇張,其實還是低估了譯詩之難。詩的“頭拙韻”(Alliteration),及“腳韻”(Rhyme),已幾乎不可能譯成另一種語文,若遇到變異的詩體,如希伯來文詩中的“字母詩”,中文的迴文璇璣,英文的“顛倒綴文”(Anagram),使“形象詩”,都是難死譯者的絕活;就是較常見的“複義雋語”(Pun),對於釋者也是頭痛的問題。好在這些都是有關技巧的,對於詩文的意境影響還不甚大。章生(Ben
Jonson)說得好,詩不能譯,可以保存語文。也許頗有道理。
好在還有可以補翻譯之不足的,是使用注釋的方法。
注釋補翻譯
但以理是個好的翻譯人。他不但譯文字,還能譯釋夢象。他曾為尼布尼甲撒王譯出“大像”的夢(參但二:),然後加以講解,指出金銀銅鐵四國度的興替相繼,並且清楚指出“必存到永遠”的第五國度(參但二:36-45)。又一次為王講解“大樹”被砍伐的異夢,並且對王勸勉。(參但四:)這都是注解的功能,是與翻譯關連的工作。
在為伯沙撒王譯出王宮粉牆上神指頭所寫的文字時,但以理的注解使文字的意義顯明得多;並且利用注解的機會,彷彿寫了一篇“跋”,或是“譯者序”,對王大加警告勸勉(參但五:17-28)。
中文和合譯本裏,夾注的小字,是為了使原文的意思更清楚,或加上另譯。在英文譯本中,則有好多種加注釋本。
廷岱爾(William Tyndale, 1492-1536),在一五二五年由英國東渡歐洲大陸時,改教運動的火焰初燃,他也只是三十剛出頭的人。他專心致力將聖經由原文譯成現代英文;加上別的人協力繼成,在一五六○年出版了日內瓦聖經。據與莎士比亞齊名同代的章生(Ben
Jonson, c.1573-1637)說,莎氏只是略識拉丁文,更少識希臘文;故依蕭伯納的說法,莎氏可列入“文盲”(依當時標準)。因此,他所讀的是日內瓦英譯聖經。由於沒有受過正式的學院教育,日內瓦聖經的注解,可能對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;更不用說當代及後代的清教徒,越洋遠播美國,且延綿及於遠代。
英王雅各一世(King James I),於一六○四年在漢浦屯宮(Hampton Court)召開神學會議。由於他自命通曉神學,也參與論辯。他痛詆日內瓦聖經是最壞的聖經譯本,因為其中的注解大不對他的口胃。在出埃及第一章21節:“收生婆因為敬畏神,神便叫他們成立家室。”日內瓦聖經注說,在王的命令與神的旨意違背的時候,順從神違背王的命令是應當的。(一六一一年出版的欽定本KJV聖經,與日內瓦聖經譯文差不甚遠,只是沒有注解。)王怕聖經注解會使人民造反,--他的懼怕並非無因--可見注解的重要了。
譯解與不解
但以理是翻譯注解人員最好的榜樣。因為他
一.不自傲:翻譯的人往往有種錯覺,以為自己跟原作者一樣高明,甚至更偉大。這是要不得的虛驕;」一有這種危險的趨向,就難免另行製造,或添油加醬,不是信實之作了。在應召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時,但以理沒有視此為炫耀學問的機會,升官發財的階梯,卻先說:“至於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,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,乃為使王知道夢的講解,和心裏的思念。”(但二:30)他這是說,自己不過是神使用的工具,是一把開啟金庫的鐵鑰匙。可惜有些翻譯的人,不久自大起來。從事翻譯的文宣士啊!切記,不求自己的榮耀。
二.求譯解:但以理告訴他的同伴,要他們同心禱告,“祈求天上的神施憐憫,將這奧秘的事指明。”(但二:17-18)證明智慧不是出於自己,是神賜的。就是到了年老成熟,功成名就,見到耶和華所定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(參但九:1-2),他還是不敢自足。見了異象,但以理“專心求明白”“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”(但一○:12)。從事翻譯的人,對疑難的事須要著心查考尋求,更要在神面前尋求,萬不可草率行事。有人把銀河(Milky
Way)譯成“牛奶道”;把“心靈固然願意,肉體卻軟弱了”,譯為“酒是好的,肉卻不成”,都是率爾操觚的結果。
三.不曲解:作翻譯的人,常為本國的人所鄙視厭惡。因為工作上與洋人接觸,而那些人多是老闆,使他們養成了“買辦”性型,雖然是聰明伶俐,但唯唯諾諾,是沒有骨頭的西崽酒保,不敢講得罪主人的話。因此,他所譯的東西,不但無足觀,也不可信;因為他慣於使用軟化,沖淡的技巧。我記得有一次聚會,講員大有能力的說:“悔改!回轉!”旁邊站的那位譯員,卻斯文的譯作:“改變意念吧!請轉回來!”那就只好全靠神的恩典了。英明睿智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宣召但以理解夢的時候,可能預感其夢之不祥,先告訴但以理“不要因夢和夢的講解驚惶。”(參但四:19)這是勸勉他直言無隱。當然,但以理對尼布甲尼撒王和伯沙撒王,都保持神僕人和使者的尊嚴,作了正確的譯達信息。這還用得說嗎?骨頭硬到敢違背王,甘被丟下獅坑的人,那會曲言討人喜悅呢?
華人文化悠久,喜歡用“婉辭”,以避諱不祥的凶詞。特別是諱言“死”字,而用別的詞代替。如:“山陵崩”是說大人物如帝后之類,死得驚天動地;“不祿”是說死了再也不能支領薪俸了;“卒”是說死是個結束,完了;也可以說“逝世”是說去了;“大行”是說去了不再回來了。這就比“死”字溫雅得多了。又如貪污是不雅的字,叫作“簠簋不飾”,表明受了賄賂,作不好祭祀的事,有人叫作“冰炭敬”,表明消解不同意見;俗語叫“送紅包”,都比賄賂好聽,受之者良心比較受用,不損其唱愛國之高調。但從事譯事的,可以不必太客氣,而且也怪為難的去找相對待的好聽話。同時,為了討人喜歡而用好詞兒,成了“曲譯”,也是要不得的。
四.不強解:今代人喜歡解說豫言,但不喜歡“不知為不知”,好像個全明白,連不知道的閉口不言都不肯,是個很可怕的現象,很容易為虛假的靈所乘。但以理說到“要將這異象封住”(但八:26),又被囑咐要“隱藏這話,封閉這書”(參但一二:4,
9)。上帝所定的時候,上帝的智慧,原不是要都給人知道,而且也有些不是人所能理解的。因此,使徒教訓人要防備有人“強解”(參彼後三:16-17),恐怕被那些強解的惡人的錯謬誘惑而墜落。
大概很少有別的語文,像中文一樣,有豐富的字眼兒,可以隨作者譯者的愛憎而更換選用,卻標示著善與惡。當然,這種標示有時是頗可爭議的。例如:“侵略戰”與“防禦戰”是對比的,都是中性字,說明戰爭的性質;但在中文裏,我們挨敵人打叫被“侵略”;反過來我們侵略別人時,則用“征伐”“聲討”等好字眼兒。“篡弒”,“背叛”,“造反”,是惡意字眼,大部份是用來講失敗的人;“起義”,“革命”,“天討”,則是好字眼,但講的完全是同樣的事。“軍閥”自然是用來稱呼不喜歡的人,那就不用說了。好像是海明威(Ernest
Hemingway, 1899-1961)說過:“走私的人,只是走私失敗的人。”所以譯者在文字上玩曲譯曲解的把戲,是常有的事,可以改變作者的原意,而作者或譯文讀者卻被蒙在鼓裏。這就是在字裏行間的“夾帶走私”。有的人在譯名上弄手腳,表示其情感上的愛憎;把印度人愛戴的領袖Nehru譯為“泥黑虜”,好像再沒有更好的方法表現自己的幼稚和缺乏風度一樣。這是“曲譯”的例子,和古時漢人侮辱少數民族,稱他們為“猺”“貊”,把人視為畜牲,真有“異曲”同工之羞。
說到譯名,我們要承認上一世紀的人譯得很典雅合宜。例如:英吉利,法蘭西,美利堅,德意志等,似是還隱含其國家之特性。看新近的譯名,我們可以有理由慨歎今不如昔了。如:尼加拉瓜,瓜地馬拉或危地馬拉,如果這些小國的人也懂中文,也可以抗議,他們將作何感想,作何反應!這簡直是半文盲買辦官僚的手筆,真是有損國體,足以表示華人的可憐。
如果說到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翻譯的高明,可稱可說的就太多了,非有卷帙浩繁的專書不可。現在且簡略的說到譯名之妙。梁發譯主的聖名為“爺火華”,顯示神是天老爺,忌邪的神,是烈火,是威嚴的主宰;我們現用的聖經則譯為“耶和華”,“耶”與“爺”古時通用同義,是生命來源,但文雅得多,“和”是“和愛”,“和平”,“華”是威嚴榮美。“耶穌”是表明神的兒子賜生命,“穌”與“蘇”同,是“后來其蘇”的意思,使人得救恩。至於“基督”,“基”是根基,“督”是監督,督率的意思;祂是基石,又是頂石,是初也是終,是至高的王。又加“大衛”,有譯本作“大闢”,固然表示是開闢以色列歷史第一個合神心意的王,但音近“大辟”之刑,“大衛”就好得多。猶大最後的王譯為“西底家”,不解自明。其他人名地名,大都譯得典雅合宜,而饒有意義,所以一般刊物文籍書冊,加以採用,而約定俗成,就是好譯作的證明。像羅馬教聖經的譯名,保羅譯成“保祿”,彼得譯為“伯多祿”或“伯鐸祿”,不但庸俗,更顯示其作官掌權的思想,叫人不屑一顧。
當然,和合本譯名中也有不理想的。如:女子譯名“以利沙伯”,寧譯“伊麗沙白”;老夫子譯名“尼哥底母”,不妨改為“尼哥德謨”。兩個女人“友阿爹和循都基”(腓四:2)等次要人名,改“猶阿嫡”和“荀都琪”自無不可。
翻譯和注解是文宣聖工的重要部份。中文既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語文,華人聖徒的任務,也相對的越重越大。特別是在這末世,大眾傳播的技藝進步,“多人來往奔跑,切心研究,知識增長”(參但一二:4),翻譯注釋益加重要。過去的歷史證明,譯文介紹思想,改變了歷史,今後必更如此。我們應該忠心信實,不要誤譯作釋;要光明磊落,正確的傳神譯意。當效法但以理,在這工作上盡忠,作得好,作得合主心意,也同有分於主對但以理的應許:“你且去等候結局,因為你必安歇;到了末期,你必起來,享受你的福分。”(但一二:13)